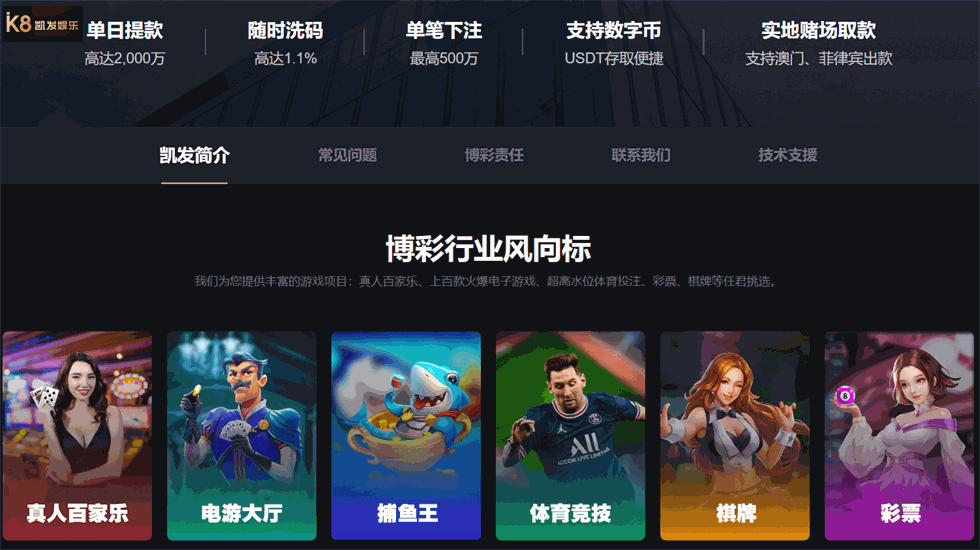菲律宾疫情总有一种悲伤让我们泪流满面

2021年的复活节,充满新生和希望的日子,然而持续一年的新冠传播,让这一个充满宗教意味的日子,蒙上了更多的晦涩。
扬·贝尔蒙特(Yang Belmonte)是一位年轻的菲律宾小哥,他接着电话,电话的另一端,医护人员不停道歉,因为医院已经没有空余床位,供其患有新冠的祖父使用。
争抢医院的生死时速
杨和他的八位家人,为了自己祖父的病情,已经失眠了3天。
自耶稣受难日以来,每个人都在做着努力,尝试在马尼拉大都会附近的医院,寻找一张空置床铺,来让自己的亲人得到妥善的治疗。
医院热线,政府热线,从社交媒体获得的新增床位的医院电话......不断的尝试,忙碌了几个小时的电话寻找,像繁忙的工蜂一样,他们与其他数百人一起,在争抢着有限的病床资源,希望他们的亲人能被医院接纳。
杨说:“这就像生死时速,我们在争分夺秒。”
他和家人们,寻找医院的范围,从马尼拉大都会一直扩散到附近的省份。
无论是北部的奎松市(Quezon)还是南方的阿拉棒,无论是4个多小时北上或者南下,只要能找到一处安置的地方,就是他们的最大心愿。
自从杨的祖父母,于3月28日被送往检疫中心以来,他的姨妈一直在照顾这一对长者,因此,姨妈同时被送往同一检疫所。
在其他家庭成员的视频通话帮助下,杨的家人照顾了生病的祖父母。尽管护士每三小时左右就会过来检查一下,但扬说他的祖父母,从来没有经过医生检查。对于被告知要留在检疫中心,以防止病毒传播给其他家庭的患者,几乎都是听天由命。
杨的叔叔和另一位堂兄以及这位堂兄的祖父母,也在3月21日对该病毒的检测阳性。
杨说:“当我们看到我的祖父血氧饱和度时,那便是我们开始寻找医院的时候了。”他回忆起脉搏血氧仪的读数曾一度下降到40%。这个数字远低于健康人氧气水平的98%,并且低于卫生官员所说的寻求医疗的指标90%。
当他的祖父的病变得“危急”时,杨的家人唯一能找到的就是一家医务室,那里有一辆急救车和呼吸机救命。
杨说:“随着复活节的到来,我的祖父在那隔离中心内,为延续自己的生命而苦苦挣扎。”
复活节星期天,卡罗奥坎的一家医院,通知杨的家人,医院现在有一张空余出来的床位,可以接纳他的祖父。
救护车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。杨说:“当我的祖父,终于到达那里时,他陷入了昏迷状态。”
两天后,2021年4月6日,杨的祖父去世了。
马尼拉大都会及附近省份,无论是2020年的疫情爆发,还是此次的第二波变种疫情来袭,无疑都是菲律宾大流行的震中,对于许多家庭来说,情况就是这样,在新冠疫情爆发一年多之后,面对第二波疫情,城市再次处于封锁状态。
与第一波疫情相比,眼下的第二波疫情,每日感染处于历史峰值,而连续几天的死亡数字,都达到了百位数,医院不堪重负,有的甚至超出了承受能力。
道路交通超载会引发交通堵塞,而医院接诊能力超载,则意味着很多新冠感染患者,至死有没有接受过医疗救治,都是一个问号。

对于许多菲律宾人而言,从3月份开始爆发的第二波的疫情,分外难熬。
无论菲裔,华裔,刷新社交媒体的信息瀑布流,就和刷新一道离别的哭墙一样,身边的朋友和家人,不断有撒手人寰的不幸发生,屡屡刷过屏幕的橘色烛光,以及一行行R.I.P,预示着告别的朋友越来越多,越来越多的家庭陷入生离死别的痛苦之中。
这次的分别,更加痛苦,因为医院的超载,众多的死亡者,甚至没有机会去寻求治疗。
那么,什么地方出了问题?
杨说:“我们不应该抱怨那些不停和我们说道歉的医护人员,因为显然没有可用的设施是事实。但是,我们也不应该成为寻找医院而不得的人,是谁让医院入院无门?”
截至4月16日,马尼拉大都会区多家医院专用床位中至少有66%被占用,根据杜克部长的通报,有六个城市的ICU病房已经处于100%满负荷状态。
据杨表示,他们曾联系邦板牙(Pampanga)克拉克(Clark)的一家私立医院,杨说,排队时间太长了,以至于他的祖父即使有床,也是第256个候补。
像许多人一样,杨的家人也曾经历过这种情况,因为他还曾尝试致电政府的“医院指挥中心”,该中心成立之初,预想是成为医院之间强大的转诊分流系统。
然鹅,指挥中心在菲律宾期间首次成立,平均每天接到300至400个电话,它只配备了两个手机号码和一个座机,这导致了基本全天都是无法接入的状态。
艰难的选择
菲律宾急诊学院(PCEM)校长康沃卡(Pauline Convocar)博士告诉媒体,马尼拉大都会一些主要医院的急诊室几乎每张病床,都被占用了数周。
在第二波疫情,开始急剧增加病例的同时,急诊科是最早感受到求诊急救压力的地方。
康沃卡博士说,有很多家庭的老人,是一家一家的集体中招,她在医院轮换工作的4天中,有3天她发现很悲伤的现实,医院的床位有限,而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一家里所有的病人,家庭成员间只能开一个家庭会议,确定谁的情况最危急,最需要优先收治。
“ 他们是一家人,当您看到患者时,都已经有呼吸急促的症状,但是你却必须硬着心肠告诉这家人,'我只能收治一个您的成员,因为那是我(床)中剩下的全部……”。
“您与家人交谈,他们来求医,症状都已经很严重,但是他们却面临一个生死选择,把生的希望留给谁?这样的选择太残忍,如果是你,你会选择其中的哪一个?”康沃卡博士说起来,不无唏嘘。
她说:“对于家庭来说,生病的父母,选择送谁入院,可能非常困难,那很痛苦。”
截至4月中旬,大都会马尼拉的所有14家私人医院中,至少有310名需要医院护理的新冠患者仍在等待病床。
14家医院,虽然只是该地区和邻近省份159家医疗机构中的一小部分,但仍凸显了公立和私立医院,在感染病例尚未减少的情况下,所承受的压力。
康沃卡博士说,有时候她接到电话,电话那头哭着求她帮忙,“亲人要不行了,已经昏了过去......要求医生行行好,给在汽车或家中等待病床的病人,插管吸氧治疗。”
她的理智告诉她不可以这样做,因为在不受控制的环境中向患者插管,可能会导致病毒传播给在场的其他人。
即便如此,说起这一幕,康沃卡博士还是哭了,这些人,还能有车有房,而那些什么都负担不起,无力开车去医院的家庭,一样面对病毒传染的风险,面临呼吸困难丧失生命的可能,然而,就这样,成了冷冰冰的死亡数字的一部分,甚至,因为死于呼吸困难,连新冠确诊数据的一分子也不是。

即使患者已经在医院接受治疗,家庭以及为他们治疗的医生和护士的处境也常常很严峻。
一名内科住院医师克里斯塔尔·莱恩斯(Chrystal Leynes)博士说,她仍然想起一名瓦伦苏埃拉(Valenzuela)怀孕的警察,她于3月中旬就诊。母亲因担心婴儿的生命而拒绝进行插管,而丈夫则向医院恳求让他签署一项放弃健康声明豁免书,好让自己进入病房与妻子厮守照顾妻子。
看着警察的老公签字的那一瞬间,莱恩斯感觉浑身被抽走了所有力气,想要做什么,但又感觉无济于事。
康沃卡博士讲,每一天的工作,有时候感觉真的是煎熬,因为现在空出来一张床,往往意味着这张床上的上一个过客,已经去向天国,在与死神抢夺生命的过程中,又一次被死神所击败,深深地无力感。
杨的祖父去世后,他的姨妈,叔叔和表弟从新冠感染中康复,但接下来是他的祖母最终需要住院。
这次,他们能够为她送医院。
“很显然,我的祖父已经没了,我的祖母也中招了,幸运的是,那家医院接纳了我们,不幸的是,祖母的症状也很严重,治疗费用是昂贵的,我们现在要卖掉祖父母的房子,以应对医院的开支。”
每次将家人带到救护车上时,杨都坦言他所担心“最糟糕的情况”,并因此感到恐惧:“我知道把他们带到医院,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救护车,我总是会担心,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。”
失去的一年
随着感染数据的攀升,越来越多的患者亲属一直在寻求社交媒体的帮助,以找到可以入院的医院,有些人则转向家庭治疗,因为医院中没有空位了。